从千篇一律到穿出自我-z6尊龙旗舰厅
阅读提示:如今走在街头,你会看到极简风、森系风、波希米亚风,会看到混搭、撞色、叠穿、内衣外穿,会看到汉服旗袍唐装,也会看到运动嘻哈——奇装异服再也换不来回头率,见惯了大场面的上海人一笑而过,彼此都习以为常。
记者|阙 政
走在马路上,迎面而来一个和你穿着打扮一模一样的人,这在如今应当算是极小概率事件。然而往回倒退四五十年,你却会看到一个中国人“集体撞衫”的世界——在安东尼奥尼拍摄于1972年的纪录片《中国》里,不管是南是北,在都市还是在农村,举国上下基本上只有五种颜色:白、灰、黑、蓝、绿。五色里没有一种是鲜艳的:绿是军绿、草绿,蓝是灰蓝、靛蓝,在西方世界眼中,千篇一律的服装,把中国人变成了一群“蓝蚂蚁”。

改革开放40年征程中,服装还见证过“中国工厂”:曾经,中国代工8亿件衬衫,才能进口一架空客380。但是现在,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“胖九”一飞冲天,有媒体起了这样一个标题:“谢谢你c919,中国不需再用8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了”。
“蓝蚂蚁”消失的背后,有着中国制造业工人大幅提升的时薪:根据德勤的数据,2005年,中国制造业工人的时薪还低于越南;但到了2015年,中国工人的时薪已经是越南工人的1.5倍以上;而印尼的人力成本甚至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。
今时今日,翻开时装的标签,你会发现“made in china”越来越少。
83分钟里换了43套衣服
国人服装意识的觉醒,和许多其他觉醒一样,发生于改革开放肇始的1978年。工业机声的隆隆作响,打破了棉布凭票供应、每人每年的定量配给;逐渐洞开的国门,让国人沉寂已久的审美意识慢慢苏醒。
爱美之心重新在国人心中集体大爆发式地蠢蠢欲动,标志性事件是1980年电影《庐山恋》的公映——这部“文革”后首部以爱情为题材的电影,一上映就引起了轰动,主演张瑜在次年拿齐了金鸡奖、百花奖、文汇奖、政府奖四大奖。

轰动,不只因为电影中出现了“吻戏”,描写的又是华侨女孩的生活;更因为片中的华侨女孩,在短短83分钟的片长里,一口气换了43套衣服——白色西装、白底紫花小洋装、桃红色毛衣加黑色喇叭裤、a字无袖连衣裙,甚至还包括泳装。
据张瑜后来回忆:“有一点别扭,就我和小郭(郭凯敏)穿着泳装,那我就有点儿不好意思,所以我就一直用这个浴巾包着,后来那个摄影师说你这么老包着,我也不知道这个曝光度什么样啊,我这么一闪,赶快一盖,就那么保守,就那么不好意思,直到拍的时候,才把这个浴巾拿下来。”
而43套服装,也是被观众细心数出来的:“有一对男女在恋爱,男生对女生说,我们来打个赌,张瑜在这部戏里到底换了多少套衣服。为了这个事他们看了好多遍电影,总是记不住。后来那个男生进场以后,就准备了一张纸,我换一套衣服就撕一张纸条,后来他知道,我换了大概是43套衣服。”
推开时尚之窗看世界
就在张瑜换43套衣服的前两年,中国服装市场迎来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位外国人:法国服装设计师皮尔·卡丹(pierre cardin)——1978年,皮尔·卡丹身穿毛料大衣,双手插兜,漫步在北京街头,被摄影师抓拍下永恒的定格——当时他的回头率,可以说是百分百。
商业嗅觉灵敏的皮尔·卡丹瞄准了刚刚打开封禁大门的中国市场,决定用“时装秀”来传递品牌的美学概念。于是,次年4月,新华社记者李安定接到了外贸部门通知,法国服装设计大师皮尔·卡丹将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一场服装观摩会。“在一个临时搭起的t台上,皮尔·卡丹带来的8个法国模特和4个日本模特,在流行音乐的伴奏下扭胯摆臀迈起了猫步。台下,则是一片蓝灰制服。”后来李安定描述了服装秀上的细节,“当一个金发美女面对观众停住脚步,突然兴之所至地敞开对襟衣裙时,台下的人们竟像一股巨浪打来,身子齐刷刷向后倒去……”
1979年,法国服装品牌“皮尔·卡丹”进入中国。有人如此形容:“当中国人下定决心推开窗看世界的时候,第一眼看见的牌子是‘皮尔·卡丹’。”的确,80年代直至90年代初的城市街头,“皮尔·卡丹”几乎就是唯一的舶来品牌,买一件皮尔·卡丹的西服,配上一条“金利来”领带,几乎就代表了当年的“时尚”顶配。犹记得满街“皮尔·卡丹”的招牌用的都是繁体字,“尔”字写作“爾”,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不明就里的小伙伴念作“甭”。
后来据皮尔本人向《环球》记者透露:自己一直有一个梦想,到中国去制造、推销纽扣。按照他的计算,中国人口超过10亿,按一人一年使用30颗纽扣计算,整个国家需要30亿颗纽扣!皮尔在中国授权代理销售的服装,使用的纽扣也都是从自己工厂买的。
这个始于“纽扣”的商业故事,最终在中国大陆创下了许多个第一:第一次举办服装表演,第一次把中国的模特带到巴黎,第一次把法国高档餐厅开到人均月收入只有几十块人民币的北京。
就在皮尔·卡丹举办服装观摩会的次年,日本和美国的时装表演队也相继来到上海进行表演,在见识了几场外国的时装秀后,上海服装总公司决定成立自己的时装表演队——1980年11月,从事新品种开发工作的徐文渊受领了此项任务。在随后的两个多月里,徐文渊走访了60多家服装工厂,在3万多名服装工人中挑选时装表演队的队员。
“在北京,宋怀桂也做着相同的工作:她是皮尔·卡丹在中国的一系列传奇的参与者和实施者,但在1981年,她面临的首个难题,也是找模特。她是为皮尔·卡丹将于1981年10月在北京饭店举行的首次面对公众的服装表演做准备。”据史料记载,“当时的选角过程听起来像是‘街头运动’:看到有个漂亮的姑娘或者小伙,就过去,先把自己介绍一番,再把模特行业介绍一番,最后问人家愿不愿来试试。最终挑选出来的一二十人,有卖蔬菜的,织地毯的,卖水果的……1981年10月,经过几个月专业训练,‘文革’后首批中国登台表演的模特,取得了超乎寻常的成功。”
中国大陆的第一支时装模特队,就这样成立了。1985年7月,这批模特在皮尔·卡丹的带领下登上了法国的t台,让西方舆论惊呼:“毛泽东的孩子们穿起了时装!”由此而来的“模特热”,也一直延续到90年代。在模特杜鹃主演的影片《纽约纽约》中,就能看到一个普通的上海人家女孩,如何经过包装登上五星级酒店的t台,如何远涉重洋寻梦纽约。
“的确良”和“开司米”
服装秀、模特儿、女明星,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国人的审美细胞。1984年,一部电影的名字直接就叫:《街上流行红裙子》。也是从80年代开始,“蓝蚂蚁”逐渐消失,棉布不再只有五色,还有一种叫作“的确良”的新型布料,像神秘的切口一样,在广大女性之间口口相传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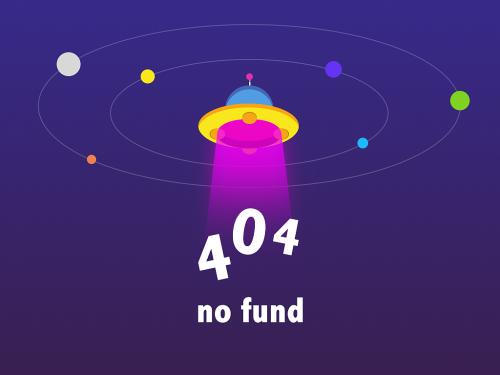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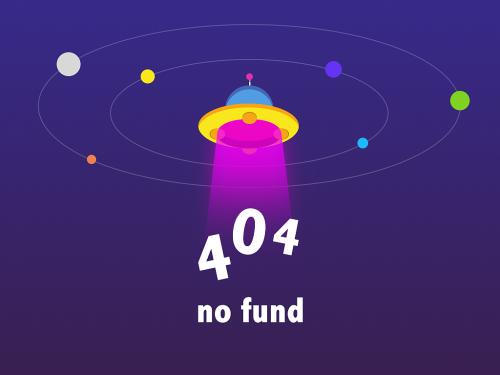
以今天的眼光来看,“的确良”就是“涤纶”的音译,在商场里买衣服,如果翻到成分标签写的是涤纶、锦纶,那多半是要放回原位的,只因它不算天然材料,较次一等。然而在当年,“的确良”就像它的名字所暗示的: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非常优良的面料,因为看起来颜色鲜艳,摸起来手感滑爽,洗上很多次仍然挺刮不走形。70年代末80年代初,中国大量进口化纤设备,由此引发了“的确良”狂潮。
而和“的确良”相似,不胫而走的还有另一种高档毛料:“开司米”。所谓的开司米,其实也是“山羊绒”的音译。相比涤纶,羊绒在任何时代都算得上是高级材料,90年代上海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以后,就常常听到家长们在讨论“开司米”了。
不过,那时候的开司米成品毛衣、大衣并不常见,更多的还是买一些开司米绒线回来,自己加工成毛衣。80后的家长们多少会织一些绒线——几大包绒线买回来,把椅子倒过来四脚朝天放好,先把绒线缠成一个个线球,然后就是各显神通的时候了:几根棒针,从简单的斜纹,到复杂的菱形纹、水波纹、菠萝花、镂空跳针……前些年某奢侈品牌出了一款天价毛衣,被中国年轻人群嘲,正因为毛衣上的菠萝花,乃是我们小时候最常见的“妈妈出品”。
妈妈们不仅会打毛衣,还会做各种衣服。80年代结婚讲究的“三转一响”四大件,其中一转就是缝纫机,可见在那个物质刚刚由贫瘠开始往富足过渡的年代,自制服装还是占据很大比例的。当年的服装店尚不如今日林立,反而可见不少布店,一捆捆的布整整齐齐地在柜台上垛成小堆,选好一款,营业员就会以熟极而流的手势拉开,用一把木尺迅速丈量好,剪刀一划,刺啦一声,布就整整齐齐地裁开,用纸一包,拿到裁缝店里,就能按照时下最流行的样子,给你量体成衣。那会儿,书店里的毛衣针法和西方服饰流行趋势,是最畅销的品类之一。
而上海妈妈们的民间智慧,还在于发明了一种叫作“假领头”的东西。顾名思义,假领头通常以细毛线织成高领或者翻领——但只有领子,底下空空如也,并没有一整件毛衣存在。假领头穿在内衣外面、毛衣里面,从外观看起来,就像是穿了两件毛衣。而且,因为假领头所费毛料极少,可以一口气织上色彩斑斓的十多个假领头,天天“翻行头”,营造出一种时髦的感觉。不明就里的外乡人,会惊讶于上海人怎么有那么多花样新衣。这种温饱年代的小心思,是上海人独有的生活智慧。现在看来,假领头不仅很时髦,还相当实用——类似于第一代保暖“围脖”。
你穿的衣服,就能代表你
等到90年代下海大潮一来,有了“个体户”“万元户”之后的城市,时尚指数也随之飙升。“假领头”日渐退出了舞台,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个体户商贩小摊上竞相登场的连体裤、健美裤、蕾丝裙、踏脚裤、喇叭裤、牛仔裤、蝙蝠衫、露脐装、破洞裤……伴随着“迪斯科”的兴盛,这一时期的服装不怕标新立异,就怕平淡无奇。
走在淮海路上,父亲会指着橱窗里的破洞牛仔裤问我:“这就是现在最流行的乞丐装,你要不要买一件?”我想了想,拒绝了。脑海里浮现出的是小时候跌破膝盖,家长们几乎都会选择去小店里买上一对印有小白兔或者小猫的贴布,贴在两只膝盖的破洞上,又好看,又能遮住破洞。小小的心里有点纳闷:怎么才过了没几年,就开始以“乞丐装”为美了呢?
街头巷尾,一种后来被称作“文化衫”的东西也在悄悄走红,最有名的莫过于印上“别理我,烦着呢”几个大字,堪称个性化思潮在传统汗背心上的再生。
这时候,比皮尔·卡丹稍迟一步的众多国际品牌也开始入驻都市:lv、巴宝莉、香奈儿、范思哲、阿玛尼……而在2001年举世瞩目的apec峰会上,各国领导人身着的对襟唐装,又引发了全国人民对于民族服饰、复古唐装的热情——与此同时,张曼玉换了23套旗袍的电影《花样年华》,也引发了举国上下的“旗袍热”。一时间,东西合璧,服装对于国人而言再无定势,连“个性化”都不必再刻意强调,人们已经根据他们的需要选择了得体的服装,“你穿的衣服,就能代表你”(you’re what you wear)。
还记得小时候,妈妈要教我织毛衣,被父亲阻止:“将来没有人自己织毛衣了,直接买就行。”他的话对了一半——当“手作”“匠心”再度流行,有人可以花一年时间,用最传统的“柿子染”来制作一块棉布,呈现阳光自然赋予的机理;有人愿意花上数十倍的价钱,请裁缝量体制衣“高级定制”;白领之间学打毛线、学做皮包也重新蔚然成风。织毛衣这件事,从节俭持家,摇身一变,成了生活美学。
如今走在街头,你会看到极简风、森系风、波希米亚风,会看到混搭、撞色、叠穿、内衣外穿,会看到热裤短到大腿根、但裤袋却要长出几分,会看到露肩衬衫、只塞一半进裤子,会看到汉服旗袍唐装,也会看到运动嘻哈——奇装异服再也换不来回头率,见惯了大场面的上海人一笑而过,彼此都习以为常。


(15).jpg)
